一幅经济世界的画面可以解释为什么公司创始人被誉为英雄。根据这一画面,经济处于正常状态,一切都在平淡无奇的平庸中进行。广大从业民众都被困在例行事务当中,该体系朝着更草率和效率更低的方向走下去。但是随后太阳升起,天才突然出现了(或者更现代的说法:从加利福尼亚的车库而来)。他是一名年轻的男性,具有运动的步态和果敢的外观,并有书卷气。根据定义(per definitionem),这个天才有一个绝妙的想法,并尽一切努力使它成为现实;不顾一切的可能性,不顾一切反对的声音,不顾体系的一切惰性,他将新事物带入世界。
如果这个画面是真实的,我们都应该感谢这些天才。没有他们,我们的想法就会陷入永恒不变的沼泽。他们使社会不断前进,他们具有“破坏性”,这在短期内可能会造成一些伤害,但从长远来看,这将使我们向前发展(从长远来看,事情正在走上坡路也是此画面的一部分)。天才的银行账户里有巨额财富是理所当然的,毕竟他们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任何怀疑这一点的人都会受到指责,是借故挑起一场“嫉妒辩论”,这些人被平庸者的嫉妒所迷惑,他们不愿承认天才的特殊性。
企业家天才的形象很少被明确提起,但却屡屡出现,特别是在涉及数字变革时。初创企业受到赞誉,就好像所有在现有企业工作的人都因此是失败者一样。“破坏”(Disruption)被置于“进化”之上,一切看似渐进的变革都被谴责为过于迟缓。那些被授予天才地位的人则适用于其他规则,例如早年脸书使用的口号“快速行动,打破局面”(move fast and break things)并未被批评无所顾忌,反而被认为值得效仿。
相反,一切与“破坏”无关,但与维持现状有关的可能的劳动形式都被贬低了。例如,为了天才们能够“死磕”其项目所必需的劳动,从运送食物到修补坑洼再到警察和政府机构维持公共秩序;所有与照顾老弱病幼有关的劳动也都被贬低了。这一切与天才的光芒相比,都显得黯淡无光。顺便说一句:现在提出关于男性和女性榜样问题的人就显得很无聊了。
在此,我们当然不应否认某些人在将科学知识转化为新技术产品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们不仅需要了解技术的可能性,而且要具备知道哪些需求可以得到满足,甚至首先被唤醒的第六感,他们要找到合适的企业形式,从而能够进入大众市场。这需要综合的技能和天赋,而这些并非人人都具备。
但是,当我们回顾孤独天才的思想史背景时,就会对他们的形象产生最初的怀疑。这一思想最重要的先驱之一是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883—1950)。他是来自奥地利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在20世纪上半叶建立了所谓的“奥地利学派”,在经济学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该学派特别强调资本主义制度的动态特性。当其他经济学家在探讨市场如何在供需之间建立一种平衡时,熊彼特则对不平衡的产生方式很感兴趣:经济周期、技术变革或经济生活组织形式的创新。
迄今为止,熊彼特最著名的概念是“创造性破坏”。这个想法比较古老,例如早在1848年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的《共产党宣言》中就已经出现。但是正是熊彼特在这个令人难忘的概念下进行了真正的扩展。“创造性破坏”的英雄不是科学发明家,而是那些在市场上实施创新的人。他们具有“创造性”,因为他们创造了新的事物并改变了世界,但同时也具有“破坏性”,因为古老的公司被新的竞争席卷,市场的游戏规则被改写。或者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所有固定的、锈蚀的关系,连同它们所有附带的历史悠久的思想和观点,都被消解了……所有静止的、停滞的东西都蒸发了……”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这些动态变化过程中的参与者是无名无踪的,其焦点是竞争和资本形成的系统过程。而在熊彼特那里,“创造性破坏”说法的背后是一个相当粗糙的人类形象。根据这个形象,被动、惰性的大众面对的是少数已走出大众的“伟大”人物。当大多数人满足于过平静的生活时,“企业家”则会受到蠢蠢欲动的野心驱使,不受社会习俗或理性羁绊,为这个世界注入新鲜事物。
这种人类形象在20世纪前几十年中并不罕见。人们对“伟人”的渴望恰巧在魏玛共和国那个混乱的年代尤为普遍。除此之外,社会学奠基人之一——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也提出“魅力型”统治者吸引大众的想法。在随后的几十年,人们以最清晰的方式看到了这种形式的领袖所带来的危险。熊彼特的“企业家”并不活跃在政治领域,而是活跃在经济领域。但作为一种类型,其与当时流传的“领袖”和“伟人”的思想有着恼人的相似之处。
有人可能会争辩说,在数字时代,领导力并不那么重要,对数字帝国创始人的钦佩是基于完全不同的事物:丰富的思想、创新精神和创造力。这些能力确实让人敬佩。那些利用这些能力为世界带来具有社会价值的创新成果的人,也应有权为自己分一大块蛋糕。难道不是吗?
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您是否想过,例如谁是互联网的“发明者”?人们有时会提到英国人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 Lee),他开发了基本构件,如网站的html语言。但是伯纳斯·李并没有因此而赚到钱,他当时在位于瑞士的欧洲核子研究组织(CERN)工作,而不是为私人公司,更不是为自己的公司工作。虽然他获奖无数,但主要为专家们所熟知。
重要的是:伯纳斯·李也并不是一个人独自在战斗。他的发展是建立在一个更大的劳动分工关系之上的,其中许多人共同努力,使计算机联网,创造了我们现在所说的互联网。这个场面绝不是互联网的特征,而是创新产生的典型方式。
人类的知识是在社会环境中产生的,而不是通过孤立工作的天才们的独立活动产生的。有关科学与技术史的研究表明了这一点。人类知识建立在过去获得的知识之上。没有电就没有互联网,没有基本物理知识就没有电的应用,而这些知识是历经数百年发展成熟的,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因此,人们完全可以发问,新发明及其产生的利润是否应该更高程度地直接流向社会,而不是被个人或公司攫取。毕竟,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这一共同遗产之上的。
尽管人类的学习过程基本上是从驯服火焰和其他早期突破开始的,但是在过去约1/4世纪的时间里,科学知识在实际技术问题中的应用取得了巨大进步。在启蒙时代,人们意识到可以利用理论知识来改善自己赖以生活的世界。根据经济史学家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的观点,至关重要的是将有关基本现象的理论知识和有关具体机制的实践知识结合形成一种富有成效的相互关系。理论和自然科学知识让人们了解了某些事物如何运作,这使得实践者可以更快、更系统地引入具体的改进措施;反过来,实践经验又为理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指引。在启蒙运动之前的几个世纪中,已经有许多单独的发现和技术创新,但是人们对它们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零敲碎打的,没有形成一个相互支持的密集知识网络。自近代早期以来,知识得到了更广泛的共享,因为它们可以通过出版物、通过许多大学和学术协会的传授进行传播。因此,知识的社会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使个人得以发展新的知识。
许多重要的科学或技术突破都是由多位研究人员共同取得的。这一事实也印证了上述观点。科研工作通常要默默地进行数年或数十年,直至达到新突破的临界点。正是这些累积的过程最终导致了新成果的诞生——而参与研究人员之一实现了这一成果。例如,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和他的同胞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同时,有时甚至一起发展了进化论的基本要素。科学或技术创新通常是现有要素和创新要素相结合的结果。毫无疑问,这种结合必须由某个人来完成——如果不是张三来做,很可能就是李四来做。可能王五也取得了同样的突破,只是他远离科学中心,掌握的物质资源较少,或者缺乏有影响力的支持者,因此无法继续探究自己的见解。
但是,历史的记忆总是聚焦在杰出人物身上: 如今的每个学龄儿童都知道查尔斯·达尔文,却很少听说过华莱士。这就扭曲了技术创新的历史,其中杰出的思想就像山峰一样从雾海中探出头来。对于拥护这种历史观的人来说,我们的首要任务显然是找到下一个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Thomas Alva Edison,灯泡的几位发明者之一,但他首先是一位优秀的企业家,因此确保了身后的好名声)或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他大力发展了蒸汽机,尽管这是建立在他人的基础工作之上)。然而,如果你仔细审视一番,定会发现这种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许多其他人的成就基础之上的,而且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如今的情况会有所不同。
在数字化领域,还有另一个因素。那里发生的许多进一步发展都具有规模效应,这意味着,当它们被尽可能多的人使用时,就会产生优势。在其他领域也可以看到这种现象,但在数字化世界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软件一旦编写好,就可以被其他人使用,几乎不需要额外费用(正因如此,如果人们想从中获利的话,必须严格保密或进行专利保护)。一个社交网络的发展离不开尽可能多的用户,他们提供的数据量越大,就越能根据他们的兴趣和愿望提供更好的服务。不仅如此,所谓人工智能的算法程序也同样可以学会在获取的数据量越大的情况下越快地完成任务。
这些效应通常意味着,那些一开始可能只领先竞争对手一丁点儿的公司最终会掌控整个市场,而且一旦它们成长壮大,地位得以确立,新的玩家就很难跟上它们的步伐。这与大量供应商之间正常的市场竞争关系不大。人们总是在讨论,攻击者进入市场的可能性在多大程度上抑制了现有公司。但是在明显的规模效应中,例如社交网络的情况似乎并非如此——如果允许头部公司简单地收购可能对其构成竞争威胁的年轻公司,至少就不会如此。不过这是数字公司运营框架条件的设计问题。
如果我们对这些思考进行总结,那么今天那些大型互联网公司掌舵人的英雄形象就不那么耀眼了。这可能听起来有些匪夷所思,但如果没有这些人,或他们决定将自己的生命投入其他事情,那么很可能其他参与者就会利用这个技术发展状况和市场形势所带来的机会。比如许多美国大学为新生提供印刷版迎新指南的电子版,并为他们提供网络交流机会。即便马克·扎克伯格没有这样做,也迟早有人会想到,只是时间长短而已。
与此同时,我们没有必要贬低这些人的成就。但关键是: 这些成就——他们把握赢利机会、抓住时机、用自己的想法激励人们的能力——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因为他们是一个更大、更复杂系统的一部分。在这个系统中,有许多其他人提供其他形式的服务。没有无追随者的领导,没有无员工的老板(通常企业创始人和老板也离不开家人私下的支持)。正是不同参与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了今天人类劳动的运作方式,因此过度美化个人是不恰当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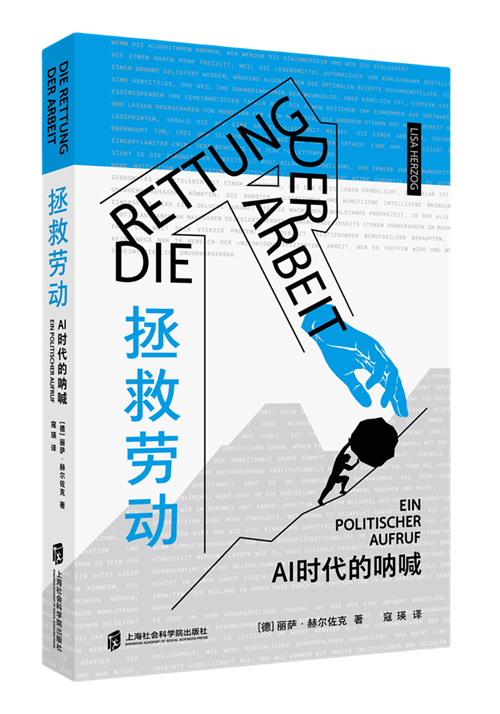
本文摘自《拯救劳动——AI时代的呐喊》,[德]丽萨·赫尔佐克著,寇瑛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5年4月,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发布。



